-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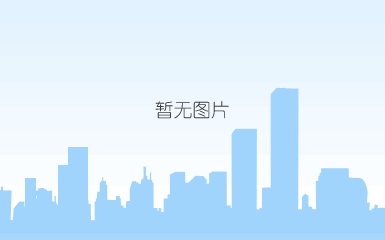
4月13日,日本共同社消息称,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持续增加的核污水处置问题,日本政府已正式确认将在两年后将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
日本的这一决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核电的种种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目前,针对于日本核污水排放具体的影响还尚不得知,但对于公共舆论和情绪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要(核废水)真这么安全的话,那运到东京湾排啊”,又或“(如果)这些水喝了也没事,那请他(声称这些水喝了没事儿的日本个别官员)喝了再说”,可见一斑。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含铯、锶、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称使用过滤设备可过滤掉除氚以外的62种放射性物质。因氚难以从水中清除,日本方面将把核污水中的氚浓度稀释到每升水中氚活度6万贝克勒尔的四十分之一以下的国家标准后再排放,整个排放预计于2041年至2051年福岛核电站完成反应堆废除工作前结束。

实际上,在核能领域,退一万步假设核电站本身能够达到百分之百安全,但核废料的处理则是一个更加棘手、甚至可以称最棘手的问题了。
目前已知的看法是,核废料在20万年之内不得流入自然界,曾有政府甚至宣称要找到一个让核废料储藏100万年的地方。很显然,这些数字不仅超出了人类文明史,也超出了现代科学的想象力。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核废料储藏基地必须能够抵挡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以及其他气候变化造成的地质变异。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构造能保证经得住自然界的沧海桑田?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埃及吉萨金字塔,也只不过有4500年的历史。这是所有准备大规模利用核能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中国同样如此。中国核工业第一、第二国际核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胥胜利曾说:“从技术层面来看,核废料主要分为高放射性、中放射性、低放射性三类。高放射性核废料含有多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高放射性元素,10毫克钚就能令人毙命。”
以日本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在遇到核废水排放问题时也束手无策。那么,此事对正在迈向核电站大国的中国,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
内陆核电应该排除在中国的发展议程之外
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一定不能在中国建设内陆核电站!如果一旦出现类似福岛核电站的严重事故,将会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制造出一个范围可观的“不宜生存区”。这个代价,中国不能付,也付不起!
其实,中国政府对发展内陆核电站目前来看仍维持着审慎态度。“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积极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在“十四五”规划中却未再出现。而国内地区已经开展内陆核电站前期工作的厂址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等。但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相关政策改变使我国的内陆核电发展进入蛰伏期。

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全球在运核电机组一半以上建在内陆地区,尤以欧洲的德法最为典型。但在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德国政府就立即宣布将关停多座老旧核电设施,随后德国议会就宣布将在2022年后彻底关停本土核电设施,迄今为止态度依然坚决。实际这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核电项目的最大隐患就是环境风险极大,切尔诺贝利及日本福岛的核电事故便是例证。尤其对于内陆核电项目来说,更是容不得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其灾难性影响将难以预计。

中国人口密集,内陆地震频发且极度缺水,修建内陆核电站无疑极其危险,也是对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对于中国在建和待建的沿海核电站,不能寄望它们受上天眷顾不会遇上地震和海啸,除了反复论证技术可靠性、安全性及选址,还要算算一旦出事,中国可能要支出多少钱,花费多久的时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后续处理费用,折合人民币上万亿元。倘若人口众多的中国遇到类似情况,清理核污染、储存受污染的土壤、核电厂的除役费用以及民众赔偿的花费,势必将远远高于日本。而且中国不具备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无法借助广大的太平洋来不断稀释被污染的废水。一旦沿海核电站发生类似事故,海洋、陆上的核污染伤害将更严重,处理时间恐怕比日本的40年要更久。
——
国内核电运行及安全监管隐患值得警惕
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中国能否避免日本那样的“人祸”。
日本政府事后在《福岛核事故独立报告书》中承认,福岛核电站事故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人祸”。除了东电公司日常管理混乱、危害预测和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员工应对失误、缺乏监管的独立性外,首相官邸多次介入处理事故导致处理事故的技术指挥系统混乱、日本政府以及危机管理体制没能发挥机能、事业者应对责任与政府应对责任界限暧昧、东电前社长的谎言等等,是导致被害没能实现最小限度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中国是否又做好了准备呢?
从国际上来看,发生重大核电事故的原因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一是对核电站设计建造运行的安全过于自信和心存侥幸,因一直保持良好运行记录,故认为严重事故概率极小,即使发生,对厂外也不会造成放射性影响;另一个便是安全第一的原则未在监管部门、核电界真正贯彻落实,在安全管理上存在漏洞,最终,小问题引发“核灾难”。
在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发生的一年半以前,与其同类型的戴维斯贝核电站就已出现类似的违规操作事件。当时戴维斯贝反应堆供应商b&w公司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备忘录中措辞强烈地指出:“事件中操作员错误地停止了应急堆芯冷却系统。这种错误如果再次发生,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尽快向所有核电站操纵员发出清晰明确的指令。”但遗憾地是,没有任何一个指令发出。不久,导致20万人惊恐撤离的三里岛核灾难发生。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的研究,在我国核电安全监管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重大安全隐患”的前期征兆,我国核电站“违规操作并瞒报运行事件”已有发生,而核安全监管部门的处理则比较滞后。
王亦楠在一篇文章中曾举了2015年广东某地和福建某地两个核电厂为例说明。2015年3月22日广东某地1号核电机组试运行一年后大修期间,操作人员违规操作,导致反应堆停堆冷却系统停运6分钟。在“实时监控系统将所有信息都自动记录在案、安全制度规定一应俱全、安全管理责任层层设岗”情况下,这个本该是一目了然、及时发现的违规事件,竟在一年多之后才被揭开。2015年6月24日,福建某地核电厂的违规操作则更危险,3号机组在自动停堆后的处理过程中,长达44小时未按事故控制规程进行注硼,最终历时59小时才达到技术规范要求的硼浓度,大大增加了反应堆意外重返临界的风险。据了解,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到福建核电项目做“同行评议”时,才发现了“6?24事件”的危险性。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核电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据王亦楠总结,有如下几类问题:
一是我国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和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于核电发展速度,已是危及核安全的严重“短板”。以前述广东、福建两件违规操作并瞒报事件显示,我国目前的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已远远跟不上核电站扩张速度,若继续无视这些后果严重的“核安全短板”,无异于是重复切尔诺贝利的“前奏”。
二是我国核安全监管部门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和核电厂实践经验,难以胜任核电安全监管。据了解,国家核安全部门曾迅速扩建过一支约1000人的安全监管队伍,但绝大部分人都是从学校走到监管岗位,缺乏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
三是高端核电人才严重短缺,人才培养速度难以支撑核电装机目标。
为了改变这种潜在的风险隐患,有业内人士建议:
1. 首先,尽快提升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可以考虑把核安全监管的主导权提升到更高层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核电安全监管。
2. 其次,尽快解决乏燃料处理和高放废物处置严重滞后的困境。按照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2025年我国乏燃料累积量将达到14000余吨。
3. 第三,需尽快确立切合国情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亟需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将堆型研发置于核燃料循环体系中科学考量,确立符合国情的核燃料循环体系。
核安全无小事,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核电站建设之后,国内需要将核电安全运行提到更高的层面来认识并强化核安全监管。
——
未来氢能社会的构建才是正途
安邦在2011年日本刚发生核泄露时就曾提出这样的思考:
“因日本的核泄漏事故,未来的全球气候谈判将会出现微妙的转变,一个选择题摆在人们面前:是要核安全,还是要低碳排放?” ——《日本核危机后,全球气候谈判面临新的选择难题》(「 每日经济 」总第3884期,2011/3/17)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净化”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一直是各国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环节。相较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其他清洁能源,核能不仅在技术上最为成熟,其供电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非其他清洁能源所能比。正因为此,核能成为所有清洁能源中技术最成熟、发电量最大的一种清洁能源。而日本的核泄露事故引发的核安全担忧,无疑向所有立志发展核电,以缓解减排压力的政治家泼了一头冷水。
幸运的是,安邦现在找到了一种可以说有能力实现鱼和熊掌兼得的途径—— “氢能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
“氢能社会”是指以氢为主要能源的经济社会,氢能广泛应用于交通、建筑、工业和电力等各个领域。

作为一种低碳的化学能源载体,氢是许多行业实现减排的主要手段,因为它能够以类似于天然气、石油和煤的方式在化学反应中储存、燃烧和结合。从技术上讲,氢能源还可以转化为目前燃料的“直接”低碳替代品,这对于排放量难以减少的行业尤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直接使用生物质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氢能利用的污染排放极小,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可能做到使用阶段零排放、全生命周期低排放。这几乎就是可持续能源利用的“终极方案”了。
当然,风险我们也不能忽视。氢气的性质限制了它的安全性,氢气的易燃性比汽油更高,因此,氢气的复杂性增加了它的使用难度;以及,某些液态有机氢载体的运输和使用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相比核电站一旦出现事故,动辄危及数十万人口,甚至产生历经数十年、以至数百年也无法消除的严重后果时,氢能还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提高看到解决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氢能有助于确保可再生电力持续快速增长。随着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降低,预期它们在未来一次能源中所占的份额将上升。在太阳能和风能占比很高的情况下,其发电量波动性将成为棘手的问题。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低碳电能占比目标。如果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到足够低,普及程度足够高,那么它们不仅可用于提供低碳电力,也可用于制造低碳能源,代替交通运输、供暖和工业原料中所用的化石燃料。实际上所制成的低碳氢能源可用于任何不是非电能不可的领域。这些优点都使氢能源成为能够很好地相互协同的技术之一,在总体能源系统层面上支持低碳能源的发展。

对中国的氢能社会建设而言,“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可再生能源制氢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并且,从发展趋势看,氢的制取方向也已十分明确,即“灰氢不可取、蓝氢方可用、废氢可回收、绿氢是方向”。在此原则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在获得氢气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少乃至没有碳排放。(至于可以从哪些方面考虑切入,欢迎拨电010 - 5676 3034 咨询安邦有关氢能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发展氢能社会的构想和路径》)
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直以来发展氢能产业、建设氢能社会的坚定推动者,安邦认为,氢能社会不仅与国家的战略决策相关,还与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更与亿万万人民的幸福与未来休戚相关,是中国应该高度重视并从现在就开始大力推动的国家级战略。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