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simple and b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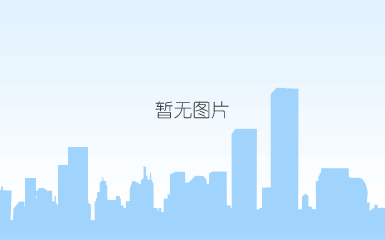
本文内容来自 「 安邦智库(anbound)“100 ”高端讨论群组 」,了解更多安邦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观点与看法、判断与预测,我们欢迎您致电 010 - 5676 3034 (工作日早10点至晚6点)咨询详情。
——

6月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视频通话,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耶伦部长讨论了拜登-哈里斯政府支持经济持续强劲复苏的计划,以及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坦诚地处理令人关切的问题。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在周三与耶伦的视频通话中,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双边和多边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非常重要,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表示愿意保持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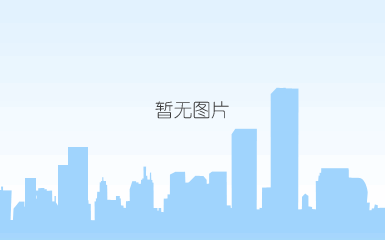
在此之前不久的5月27日,刘鹤副总理曾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一周之内,身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分别沟通,在当前中美地缘政治关系仍然恶化的背景下,中美主要财经官员的“频密”沟通显得突然。对于只盯着自媒体来了解世界的人,可能会对中美官员“突然”加强沟通感到诧异。但对于长期追踪、并时刻关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最新情况的「安邦“100 ”研究团队」来说,这些都可谓有迹可循。

图丨事件追踪时间轴 ·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早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安邦就曾给出建议——《安邦观点:“就‘第一阶段协议’展开重新谈判”或是北京与拜登政府重置中美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2021/1/27)。而且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建议高层就“第一阶段协议”与美国进行重新接触的智库机构,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我们认为这一建议得到了重视。尽管时间上节奏上似乎还能更好。
我们认为,近期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多次对话表明中美关系在一定框架之下的适度缓和,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这些变化也再度显示,大国关系从来都是多层次的,表面的外交表态、政客们的相互攻讦,都只是两国关系的层面之一,数十年全球化进程构筑的大国关系,尤其是相互需求较高、与政治相对较远的经贸关系,并不是能够轻易脱钩的。
——
以下部分内容节选自安邦“100 ”文章——《安邦观点:“就‘第一阶段协议’展开重新谈判”或是北京与拜登政府重置中美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2021/1/27)。
——
自拜登上任以来,除却集中精力应对国内事务外,拜登政府也在全面审视特朗普这四年留下的外交遗产。仅在上任后的一周内(截至1月26日),华盛顿已经就“新中东和平计划”、“跨大西洋关系”、“印太同盟”、“中美关系”及“美俄关系”等多个议题做了提纲挈领性质的表态:
自1月20日至1月26日,华盛顿多位高官就中美关系表态,称对于“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一判断,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不同,但拜登政府会采取更加合理的手段来巩固美国利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造一个“意识形态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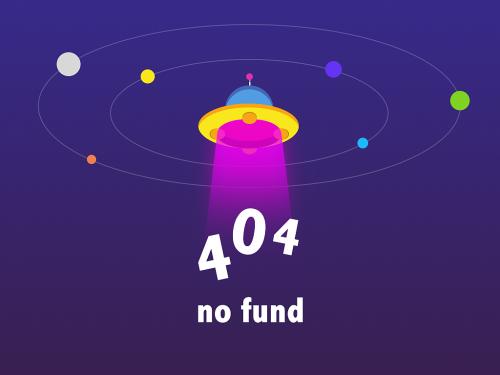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还公开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对美“隔空喊话”后,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受其影响。
1月23日,新任防长奥斯汀与日韩防务长官通话,强调美日韩同盟的稳固和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1月24日,美国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以色列通话,强调拜登政府将在地区问题上与以色列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地区正常化;
1月24日与25日,拜登分别与默克尔和马克龙通话,强调要重建“跨大西洋关系”;
1月25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与沙利文的电话中讨论了延长军备条约(new start)的问题。此前,拜登团队已对外表示自己希望延长这份美俄之间仅存的军备条约。
综合来看,迄今为止,拜登政府所释放出的外交政策路线信号与安邦智库(anbound)的判断基本没有出入。由于国内危机和建制派本身的思维特点,拜登政府目前实际上处于一个外交政策路线的构思和准备阶段。按照“亚太再平衡”的历史经验看,这一阶段的时间可能在6-12个月左右。换言之,对于世界上所有想和美国打交道的国家来说,目前正处在一个有可能影响到美国未来政策的时间窗口中,因为按照建制派的特点,一旦他们拿出了最后的系统性方案,想要再从趋势上改变美国的政策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安邦在1月份时就已经表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就‘第一阶段协议’与美国展开重新谈判,借此推动与美国展开实质性接触,以这一具体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锚点和出发点,尝试‘重置’中美关系。中国需要抓住时间窗口,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成型期就与美国形成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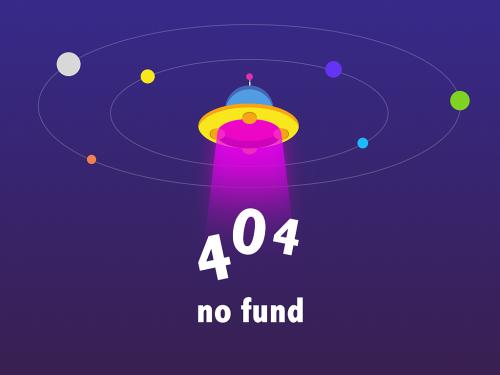
——
问题在于,中国应该如何打破在新冠疫情后中美双方各方面交流几乎彻底隔绝的困局呢?
我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考虑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政治风格和特点。从过去四年的历史经验看,特朗普政府并不符合美国一贯的“从细节出发”的特点,无论是美朝领导人的两次会谈,还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谈判,再到表面上由美国推动但实际上由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主导的新中东和平计划,特朗普追求的是政策的战略价值和宣传价值。然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并不“美国”的政策路线,导致特朗普的许多政策都遇到国内阻力,最后陷入僵局。但对拜登政府来说,这支几乎清一色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团队,其政策风格无疑又重回过去的路线。这从拜登团队并不急于发表对中美关系的宏观判断就可以看得出:他们需要首先审视过去和现状,然后在理性推演的基础上找到一条被认可的政策路线。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想要利用拜登和特朗普这段“转换期”给双边关系重新定调的国家,必须也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在特朗普时代通过“关系”或者“个人因素”来撬动美国政策的尝试(例如以色列通过库什纳、俄罗斯通过朱力亚尼等等)在如今几乎不会成功。在这方面,俄罗斯再一次做出了非常迅速的调整。在整个特朗普时代,普京所追求的就是通过“打动特朗普”从而给“美俄关系”重新定性。尽管因为美国国内因素的干扰,普京的尝试最终没有成功,但客观来看,这种方式在方向上没有大问题。在过去四年,普京很少提到美俄关系之间的具体问题,相反,所有涉及到具体问题的协商和谈判实际上都是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完成的。

但在拜登当选的当天,俄罗斯方面就宣布,希望在延长新start条约限制核武库的问题上,能与美国新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进行“更富建设性的”合作。莫斯科方面表示:“我们希望美国新政府在与我们对话时能表现出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在外界看来,这种转变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当然,俄美之间仍然存在某些结构层面的矛盾,短时间内不会因为任何人为因素而转移(除非普京提前退休)。另一方面,能够谈就比彻底隔绝要好,因为拜登政府同样不希望核军备体系进一步解体。换言之,俄罗斯利用了拜登团队相对次级但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需求来稳定美俄关系。这种尝试也得到了沙利文的回应。这就把美俄关系拉回到了“专业范畴”,从而给两国关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险。据克林姆林宫方面的消息,美俄两国领导人在1月26日首次通话后,已经就延长军控协议达成了一致。尽管拜登在对话中提到了一系列让普京感到为难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对纳瓦尔尼的逮捕),但总的来说,普京还是给拜登时代的美俄关系开了一个好头。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也可考虑就“第一阶段协议展开重新谈判”这一问题与美国展开实质性的接触,从而实现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的 “重置” 。

第一,在当前现实下,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已经不具备继续维持的可能。在本质上,这份协议的目的在于:中国出让一些物质层面的利益,换回中美关系的一段稳定期。但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原有节奏,中方如期完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特朗普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中方目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完成这份协议。
第二,第一阶段协议本身就不是基于理性推演而达成,它的核心实际上是让特朗普“感到满足”,而不是真正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拜登政府实际上也存在进一步“修订第一阶段协议”的诉求。退一万步说,如今的华盛顿起码没有理由抗拒这种接触。
第三,如果仅仅是重新就具体的贸易额问题展开磋商,拜登团队并不会买账。首先,这相当于给特朗普的外交成绩添砖加瓦,其次,拜登团队寻求的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如今的拜登团队中很大一部分都曾经历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及其他一系列双边对话,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与中国接触,但他们对中国 “迟迟没有实际行动” 感到愤怒。这些人在私下甚至如此评价过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特朗普)只是用了一种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沟通”。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谋求中美关系重置的同时,中国是否能真的做出一些实质性“让步”。
针对这个问题,《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历程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中方愿意继续改革开放,但类似的谈判必须要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因此,从中国来看,与美国重新修订 “第一阶段协议” ,对具体的数字部分作出调整,同时增加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这是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成功可能性的。
第四,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就修订 “第一阶段协议” 达成新的共识,还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1)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式翻过了“特朗普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同时,这符合中国与拜登团队的诉求。
(2)同《中欧投资协定》一样,这是一次极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证明中国并非像西方个别势力所渲染的那样“顽固不化”。
(3)如果能直接解决与美国的经济矛盾,有可能复制1976年“越顶外交”的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重新校准美国在诸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地区问题”上的政策偏向。
(4)最重要的是,即使谈判短时间内难以取得成果,只要双方的接触没有中断,对如今的中美关系来说就是好事。
第五,就此问题与美国展开接触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政策负担。逻辑上,在中国尝试接触后,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可能性:
(1)谈判成功,中美关系重启;
(2)谈判陷入僵局,但谈判本身为中美制造了更多接触机会,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3)谈判失败或者美方拒绝回应。
然而,即使出现最不理想的情况,对于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首先,中方向美国和世界释放了“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其次,中国基本可以确定,即使是相对“温和”的拜登政府,也已经放弃了与中国进行协商。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探知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外政策。因此,类似的尝试对中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政策负担。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有必要就重谈 “第一阶段协议” 与美方展开实质性接触,以这一具体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锚点和出发点,尝试 “重置” 中美关系,而目前双方的“频频”对话沟通也正逐渐验证了这一点。至于谈判的核心,安邦“100 ”研究团队认为主要在于这两点:一方面调整原有协议中的不合理内容,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结构性的调整,进一步推动国内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 “重置” 中美关系。
最后我们想再次重申的是,紧抓目前的窗口机会,或许,将会大大消除“对抗”成为两国关系主旋律的可能性。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 the end —

